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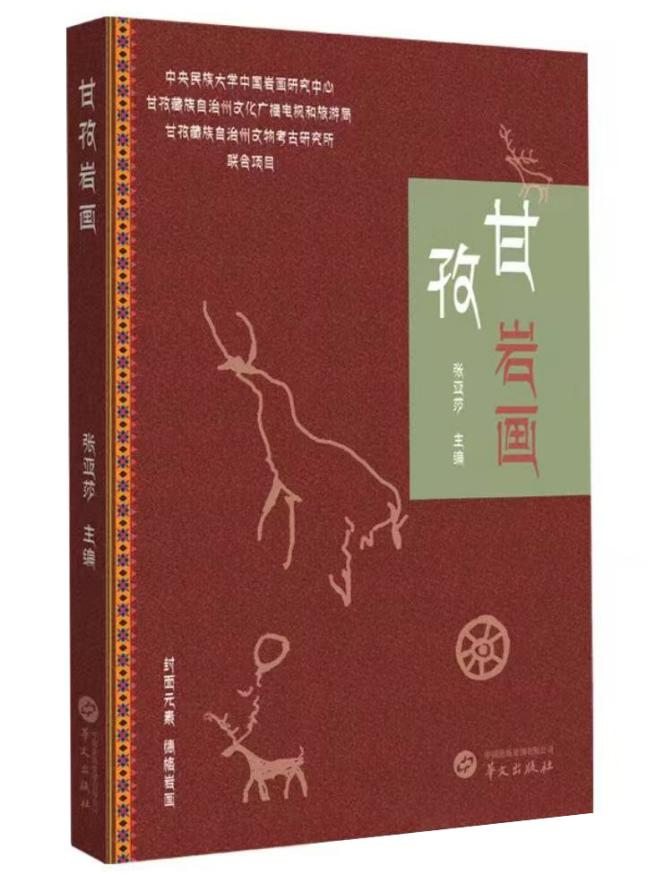
图为《甘孜岩画》
【编者按】近期,《甘孜岩画》学术专著出版。该书以全彩色印刷形式将川西高原隐秘千年的史前文明展现给大众,为近年来岩画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果,书中收录数百幅高清岩画图像,从北至石渠的苍茫草原,到南至得荣的险峻峡谷,甘孜州全境岩画的壮丽遗存首次系统性亮相。为此中国西藏网记者专门采访了该书重要编委之一周行康老师。
记者:您是如何对岩画研究产生兴趣的?能够分享一下触动您投身这一领域的契机吗?
周行康:我个人跟青藏高原结缘时间非常长,1997第一次进藏,作为一种爱好,这段时间以高海拔攀登为主。从2004年开始,我参与发起一个慈善基金会,面向青藏高原做基层公益,主要工作地区在西藏阿里,十年间我每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阿里基层做落地项目,那时候经常下乡,阿里7个县37个乡镇我基本都跑完了,在关注这个区域的同时,我也对青藏高原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兴趣。2006年夏,在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到日土县的途中,我第一次看到了219国道边上的“日姆栋”岩画,面对这些岩画,我非常想得到一些答案,这些岩画是什么人画的?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后来又去了哪里?他们有没有成为现代高原民族的祖先?当时我就立刻去查找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国内外有关青藏高原史前文化的记录非常少。同时我也去请教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国内研究青藏高原岩画的前辈陈庆英先生、张亚莎老师、张云老师等,他们的鼓励是让我日后得以深入研究这一领域的一个契机。
这些岩画还有多少?它们在哪里?或许青藏高原岩画会给青藏高原史前文化带来一个新的解读角度。
记者:您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甘孜州岩画的探查情况?
周行康:青藏高原岩画的发现大致是从西到东的一个过程,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阿里地区的岩画产生了重视,包括那曲在内的广义羌塘区域。前几年在青海玉树州也发现了大量岩画,甘孜州所在的大横断山区,这一区域的岩画在过去有一些相对零星的发现。
甘孜州是大横断山脉的核心地带,2021年我和张亚莎老师去了甘孜州石渠县,是甘孜州最偏远的一个县,更靠近青海一些,我们发现石渠岩画跟整个青藏高原岩画是一个大体系,甘孜州岩画会不会还有更多没被发现的?虽然甘孜州18个县,已经有零星的一些记录了,但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系统的调查研究对象推进起来。
2023年在甘孜州文旅局的邀请下,我和张亚莎老师还有其他学者组织了一个比较大的团队,开始对甘孜州岩画做正式调查。甘孜州的岩画一类是石刻类岩画,一般归到新石器时代;一类是更加珍贵的涂绘类岩画,一般归到旧石器时代。整个青藏高原25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里,能够确定年代、且能够系统化深入研究的旧石器岩画在当时还是空白,这种线索就非常重要。
2023年至2024年,我五次前往甘孜州18个县做了六轮岩画实地调查,且作为主笔人之一把调查与研究成果展现在《甘孜岩画》这本书中。在成书过程中,我们还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些都是后话。

图为2021年8月10日,周行康与岩画学家张亚莎教授(左一)在甘孜州石渠县阿日扎岩画调查现场 摄影:丁正男
记者:您认为《甘孜岩画》这本书最大突破是什么?
周行康:2023年6月,在海子山管委会巡山团队提供线索指引下,经过数次实地调查,我们在“海子山-格聂”区域发现了红颜料涂绘类岩画群。通过邀请国内考古权威机构来现场采样、并经实验室测定,我们确认这批岩画是距今8000年前的古老创作。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石刻类岩画的测年还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青藏高原的石刻类岩画,一般推断为距今3000多年,因而这批更久远的旧石器时代的“海子山-格聂”岩画就显得更有意义,而且它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同类风格岩画中海拔最高的岩画——位于海拔4721米的高度。
其次,我认为甘孜州岩画是整个青藏高原岩画的一个缩影。截至2024年年底,我已经实地调查了青藏高原183个岩画点,包括很多新发现的点。甘孜州中路和北路以石刻类岩画为主,南路以涂绘类岩画为主,这和青藏高原地区的岩画分布非常相似:即中部和北部以石刻类岩画为主,结合少量涂绘类岩画,往南大部分为彩色红颜料的涂绘类岩画。因此我们推断:新时器岩画类人群大部活跃在青藏高原北部、中部;旧石器时代的岩画类人群主要活跃在青藏高原南部、少部分在西部。这两类人群在时空上可能并没有过交集。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甘孜州是旧石器时代人群上达青藏高原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甘孜岩画》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更是甘孜地区人类艺术创作史、文化史的有力见证。

图为2023年6月24日拍摄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聂岩画群”大环境,远处为格聂群峰

图为2024年12月27日最新发现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聂岩画群”旺格沟岩画采集到旧石器的现场
记者:书中涉及的岩画是如何被发现的?
周行康:大部分的岩画线索是当地人提供的,他们会发现和做简单记录,但不属于正式调查。有时候大家可能也不确定这些到底是什么,我会拿着岩画资料照片一一询问。还有一部分岩画是我独立发现的,在跑了很多岩画点之后就有经验总结,不管是石刻类岩画还是涂绘类岩画,我认为绝大多数岩画点的最初选址和狩猎有关,少数与居住有关,古人在岩石上刻、画下动物图案做标记,以提醒族人这里有猎物出现,或是祈祷猎物再次出现,也有一些可能是不同部族狩猎范围的界定标记。大部分青藏高原岩画的选址即为狩猎场,因此通过观察山体朝向、山体与湿地山谷的关系、岩画点之间的大概距离去判断可能存在的岩画点。

图为2023年6月22日拍摄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聂岩画群”环境

图为2023年7月8日,周行康与南京师范大学测年专家邵庆丰教授(右一)、海管会孙康寿主任(左一)在岩画测年采样现场
记者:甘孜岩画的风格反映了怎样的史前交流?
周行康:甘孜州石刻类岩画与青藏高原其它地区岩画的共性非常强,甘孜州石刻岩画内容以大角鹿、岩羊等野生动物为主,野牦牛不太多,均为古人的猎物;青藏高原中西部亦是如此,只不过大角鹿比较少,野牦牛占比最高;高原各地的岩画,有时候会出现狼等对古人类有危害的动物。甘孜州的石刻岩画有个新特点,从甘孜州丹巴县往道孚县至德格县,有一些新的抽象符号延续出现,这些符号已经脱离了狩猎的生存需求,我们初步判断可能与青藏高原的早期宗教及民间信仰相关,这种符号并不是普遍出现的,经过对比发现它与玉树方向有一定的关联。从岩画的角度来讲,它表明甘孜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
甘孜南路的涂绘类岩画也揭示出两个现象:一是旧石器人群在青藏高原消失的时间非常晚;二是从岩画分布来推断,这群人是从低海拔地区迁徙上来的,这意味着甘孜地区人类交流活动可追溯到史前的旧石器时代。
岩画也体现着隔代传承的特点,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群会在同一块岩石上留下不同的画记,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实现着跨时空交流。从中可以推断,石刻类岩画也是青藏高原石刻艺术的源头。

图为2023年6月24日拍摄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聂岩画群”海1岩画中独特的野猪、人物、爪印图像
记者:您认为岩画研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是什么?
周行康:我们现在看到的岩画,有很大一部分原始刻画动机是记录野生动物,比如高频出现的野牦牛、岩羊、大角鹿等,还有一些能伤害到古人的猛兽如狼、雪豹、野猪,古人要搞明白他们的食物在哪里,伤害他们的动物在哪里,才能在这个区域繁衍生息。海子山是青藏高原目前最完整的冰川遗址,有1145个冰川形成的小湖泊,所以叫它海子山。因为太高、太荒,现在的老百姓只利用其中少部分区域为夏季牧场,其他则只有采虫草的季节才上去。而在海子山这片高海拔台地荒原上,古人类却是广泛生存的。从海子山现存的洞穴岩画、岩棚岩画来看,古人是定居在这个区域的。古人对环境的适应性和把控性超出我们预期,这是否启示我们现代人类也要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要保护好自然生态,把握好人类繁衍生存需求与向环境索取之间的关系。

图为2023年6月22日拍摄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聂岩画群”阿莎贡嘎岩画周边环境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青藏高原的岩画情况。
周行康:西藏7地市里,阿里地区的岩画得到比较早的发现与重视,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在做其他考古项目时发现了这个现象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然后是包括那曲在内的广义羌塘地区。青海玉树州的岩画在十年前开始得到比较多的重视,主要是本地的藏族同志在认真地调查研究。最近三、四年,甘孜州的岩画在当地政府重视、专家学者的参与下进入上升趋势,甘孜州涂绘类岩画的测年工作是走在青藏高原岩画研究前列的。目前看青藏高原西、中、东三个重要点位已具备规模和形态。
在西藏除阿里、那曲外也都有零星的发现,我以个人的身份也做过一定的调查。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的环境难度相对较小。难度大的是昌都市和林芝市,高山深谷的地理地貌不便于去寻找,会发现得慢一些。
青海的海西州和环青海湖,有少量的岩画发现,我也去做过现场调查。环柴达木盆地区域近几年做得不错,当地团队做了一次比较好的发现。果洛州这两年也有新发现,我正在协助当地做相关探索,但是数量非常少,应该与岩画人群的分布有关,很可能岩画人群在古代经过果洛这边相对少一些。
云南金沙江流域岩画和海子山岩画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均属于旧石器风格,但海拔低很多,相关发现也做得不错。
四川阿坝州的岩画目前公开的信息比较少,虽然我还没去调查过,但我相信是有的,需要找一个突破点去寻找。甘肃的高原区域目前也是类似情况。
另外,我相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辖的青藏高原部分,即昆仑山脉中段两侧,也应该存在着一定的石刻类岩画,有待进一步发现。
记者:您认为岩画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人工智能是否改变这一领域?
周行康:岩画研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测年。涂绘类岩画现在已经可以测年了,但是石刻类岩画不能直接在岩石上获得有效采样,突破石刻类岩画测年的技术瓶颈就显得很重要。
我认为岩画研究跟整个人类学研究各学科都是相关的,要和其他学科融合。比如,根据青藏高原牦牛驯化、扩散的时间,来推断岩画人群收缩范围的时间;如果能在岩画现场找到匹配的古人类DNA材料,那么不仅能够测出岩画的年代,还能测出岩画人群的人种,这将是很重要的突破。
青藏高原岩画研究领域最急缺的是基础数据库,如果能够把大家采集的数据放到一个数据库里,包括但不仅限于GPS点、周边水系、岩画照片等,那样的话,人工智能就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有些图形有相似之处,有些刻痕有相似之处,但可能距离特别远,关联之后可以启发我们去更多的思考研究。
记者:回顾整个过程,您最想分享的感悟是什么?
周行康:岩画是人类文化史的“活档案”,是人类艺术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调查与研究具有多维度重要意义。青藏高原岩画广泛存在于交通比较困难,自然环境比较艰苦的地方,它需要当地群众和游客更好去认识它、珍惜它、保护它;需要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携手探查与研究,亦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的共同推进与支持。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当地给予的支持,感谢协助我们做一线调查的所有朋友们,没有你们,就没有《甘孜岩画》这本书的顺利出版。(中国西藏网 记者/赵佳 邹慧 姚浩然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图为2023年6月22日拍摄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聂岩画群”阿莎贡嘎岩画上的岩羊图像

图为2023年6月22日拍摄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聂岩画群”阿莎贡嘎岩画上美丽的大角鹿图像

图为2023年6月22日拍摄的甘孜州“海子山-格聂岩画群”阿莎贡嘎岩画上美丽的大角鹿图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