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辈子好像都没离开过文学,我也离不开文学了。”这是吉米平阶常常向记者诉说的心声。
他追忆躺在废旧图书藤编筐里的童年,怀念在大学燃烧的诗歌激情。他谈着过去,谈着援藏时意气风发的工作劲头,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步入蓬勃时期的文学思潮,感慨有幸见证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洪流。但他不是随波漂流的一叶扁舟,在文学求索的道路上,每一步都由无数斟酌与满腔热爱浇铸而成。
后来,他依赖写作抓住思绪流动的瞬间,记录时代跃动的脉搏。用他的话来讲,这是一种“控制不住的欲望”。作为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原主席,吉米平阶的讲述,正是无数与时代浪潮同频共振的文学人的缩影。他们不断提笔,不停落笔,字字句句皆为西藏注脚。

图为吉米平阶
藤编筐里的童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城内,刚放学的吉米平阶又偷偷溜到新华书店的仓库,翻进大藤编筐的旧书堆里,在故事的海洋中游荡。一直到母亲因等不到他回家而去寻找,才发现小吉米已经在筐里抱着书睡着了。
“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那个书籍很难获得的时代,作为新华书店职员的父亲给予他的这些“小特权”,让他从小就对阅读产生了浓厚兴趣。直至今日,坐在悉心打造的书房中,他仍对《中国历史常识》小册子中的故事记忆犹新,怀念着一知半解、洋洋得意地把那些故事讲给同龄人听的“说书童年”。
对吉米平阶来说,那是个激荡但厚积薄发的时期。“炉城四十八锅庄”描绘了康定曾作为茶马古道上汉藏贸易商埠的盛况。这48家锅庄(即旅馆驿站)不仅为远道而来的客商提供食宿,还充当钱庄之用,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交易枢纽。“茶马互市”让这座小城迎来了经贸的高峰,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随着时间推移,虽有衰落、跌宕,但这种多元文化交融带来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图为炉城四十八锅庄图景,图中地点为1929年康定北门市场 来源:甘孜日报
多年后,吉米平阶总以“文化交融的受益者”形容自己。多民族聚居的家乡以包容开放的性格塑造着他的文学风格,也为他后续创作注入源源不断的灵感素材。他在公众号上连载的短篇小说“阿古登巴如是说”便以康定为原型,其中不少角色都从记忆中的家乡提取派生而来。“当然他们也都是虚构的。”吉米平阶笑着说,却不语笔下人物立体而丰满的灵魂。
二十世纪末的文学探索
从康定到北京,要先坐大巴到成都,再转乘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1979年初秋,坐着硬座整整挨过两天一夜的行程后,吉米平阶抱着装有中央民族学院(即如今的中央民族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书包下了火车,“然后就这么还晃着神,一路叮叮咣啷就到了宿舍”,他回忆着北京初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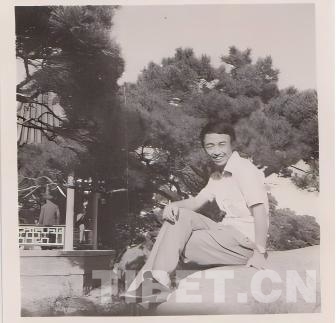
图为大学时期的吉米平阶
吉米平阶开启写作,正源于这一种极其敏感的思绪。来年暑假回家,他坐上从泸定开往康定的老式客车,客车吱吱呀呀地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头。“五十多公里的路程摇了两个多小时”,当他终于看到流经家乡的折多河时,归心似箭化作难以言喻的情绪,于是便以《折多河》为名构思了一首小诗。回乡后,吉米平阶拿着作品拜访文学启蒙先生张央。当时张央已然在康巴文坛赫赫有名,在他的指导推荐下,《折多河》后来发表在《贡嘎山》杂志上,“这是我第一个印成铅字的作品,得了十几元的稿费,还请舍友们吃了一顿涮羊肉”。

图为在民族文学杂志社任职期间,吉米平阶(左一)和同事合影
此后很长的时间里,诗歌成为他们那代人袒露勇气的窗口,也成为吉米平阶寄情抒怀的重要载体。诗中,有北京的烟火和遥远的家乡,有旺盛的思潮和飘摇的时代,不过,更多的还是他和自己的对话。毕业后,他如愿成为一名文字工作者,加入民族文学杂志社,在小说室分管西南片。吉米平阶说,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文学选择了他。
1997年,吉米平阶的首作出版。“读小说、编小说,时间久了,慢慢就觉得有些东西用小说来表达,有点意思,于是开始学写小说,就有了《北京藏人》。”尽管《北京藏人》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但过去几年,他从未停止过对小说的琢磨和探索。
吉米平阶在北京的那阵子,正值全球文学思潮涌入国门,斑斓驳杂、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就这样明晃晃地铺展在众人眼前。“它(小说)一直是一股风潮接着一股风潮发展的”,西南片区的文学发展亦是如此。作为小说编辑,吉米平阶明显感受到当时西藏文学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之深,“甚至我们很多作家也在刻意制造‘神秘’的标签,来表达遥远和不为人知的西藏”。
对这类猎奇作品的批判声音此消彼长,2006年,西藏的神秘面纱逐渐被真正揭开。那一年,“世纪工程”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我有一个梦想”
2004年,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援藏干部,吉米平阶前往西藏文联任职,主管西藏作家协会相关事宜。一间小办公室、三个人和一股强烈的冲劲为他今后履职西藏埋下了种种机缘。
三年任期间,他不停开展调研汇报,推动各省市作协对口援藏工作,“慢慢地,西藏作协的工作就恢复起来了”。援藏换届时,他和同事们正忙于西藏文联的换届工作。忙完那一阵,援藏轮换工作也结束了,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将任期延长了一届,后来在家人支持下,干脆就留下来了。

图为在昌都市叶巴村驻村期间,吉米平阶(左一)正在调研
就这样,吉米平阶在西藏一待就是近二十年,见证了西藏文学的再次复苏和西藏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2012年,他作为西藏“强基础惠民生”工作队成员,在昌都市叶巴村与百姓同吃住的经历,让他完完全全“弥补了基层生活经验的不足”,感知到西藏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行式”发展,并以此为土壤撰写了一部报告文学《叶巴纪事》。
从叶巴村返回拉萨的路上,吉米平阶陷入了绵远的思绪中。在《叶巴纪事》后记中,他如是写道,“我梦想有一天,家家都住进改造好的房子,不要那么大,但既干净又明亮;我梦想科学家们能发明一种简单的发电装置,提供给村里充足的电能,提灌上江水,世世代代临江而居的叶巴人,再也不用看着滔滔的怒江天天为水发愁……”如今,西藏的发展成就已然打消了十年前他对这些梦想是否能实现的惶惑,百姓生活富足、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连带着文学也随之愈加繁荣。

图为驻村期间,吉米平阶(右一)正在和当地村民交谈
在西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吉米平阶感觉不仅是在参与完成一份工作,而是整个人的文学观都受到了巨大的锤炼。曾经聚焦在“己”的笔墨,如今都流淌在了祖国的大地上,“过去神秘化的东西少了,更多是真实的、鲜活的内容。”他把这种转变归结为紧跟时代发展的必经之路,以及当下根植在心中的文化自信,“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璀璨的明珠,赋予我们的底气,不是一般的。”
当年抱着写满诗歌稿纸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成长为西藏文学界的前辈。回首吉米平阶的文学履痕,无数个时代潮涌中奋力拼搏的瞬间仍在熠熠生辉。他曾站在西藏文学舞台的追光里,如今,这束光里有了更多年轻的身影,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当前西藏文学“新人辈出”的势头,坚定且欣慰地笑着:“大作品还在后头呢!”(中国西藏网 记者/边子捷 文中未注明来源图片皆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手记:
成都深秋的一个午后,退休后的吉米平阶正如往常一样赋闲在家,写一些关于新作品的素材。记者与他对话的两个小时,像是打破日常节律的一枚石子,激起了记忆中那段“躺在藤编筐里”的往日涟漪。
这场访谈缘于今年7月。那时,吉米平阶个人公众号上的连载小说被选编出版为《藏地履痕》,作为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献礼。他与西藏文学之间的羁绊,不仅见证了文学本身的生生不息,更记录下了西藏波澜壮阔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从他的经历中,我们感受到了西藏文学与时代共生的蓬勃力量,看见了西藏文学工作者由他述到自述的转变对“真实西藏呈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西藏文学以纸笔,凝聚起民族情感认同,将西藏故事融入中国发展的大叙事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滋养。通过时代人物的故事缩影看见西藏,正与“口述西藏”的栏目宗旨不谋而合。
访谈最后,记者问及是否还会有其它的创作计划,吉米平阶笑着说:“还想写一个长篇,不过题材暂时保密。”无论是康定的童年、北京的求学经历,还是西藏履职的岁月、成都的退休时光,文学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在悄然间汇入了西藏文学的长河。